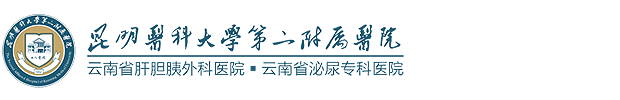题记:医院不仅仅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地方,也是一个向死而生的地方,而护患的沟通是一场场双向的治愈和成长。
首次“交锋”
成为一名正式的心血管内科护士转眼已经小半年,冬去春来,日复一日的护理工作中有时会感觉到时间的慢行,但有时一个小憩也会顿感时光匆匆。今年三月末,天气乍暖忽寒,像往常一样的很多个夜晚,我收拾好状态准时出门,到医院,进科室,换工作服,接夜班。交接班时,一位今天新收治的患者遵医嘱搬床至监护室继续治疗,只见一位中年大叔背了一个很大的背包,自己提着水杯和日用品,步行到了他的新床位,看起来精神奕奕,全无病态。交接班的老师也逐一交接了他的基本情况“患者周某,男,67岁,需进行心率监测,但患者以影响睡眠为由拒绝心电监护,拒绝吸氧,自备氧饱仪,会自测监控心率等。”一般收治到这样医从性较差,角色行为缺如的患者,我们医护这边都会尝试多次的进行沟通,作为夜班护士,我也拟写好护理的沟通记录到床旁与患者再次进行沟通。
我来到患者床旁,向患者进行了自我介绍以后便开始谨慎地询问:“您为什么拒绝使用心电监护和其它一些基础治疗?”患者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抵触,心平气和地回道:“仪器的使用影响了睡眠质量,反而会让我休息不足,另外我自己很不喜欢这种被束缚感,感觉很不自在。”大叔态度平和但又坚定,我只好循序渐进的去进行其它话题的沟通,“大叔,您是感觉到哪里不舒服来住院的呢?”大叔依旧和缓地说:“我来医院做核酸检测、体检,还准备出差呢,但是打心电图时发现心率很慢,这个情况呢我自己是知道的,大概是有近两年了,但医生很严肃的要求需要住院,其实我近前外出工作的时候也感觉到了体力不支,容易疲乏,所以看医生态度坚决,我也想不如就来把这个病查一查……”我继续问:“那您平时都是用氧饱仪自测心率的是吧?晚上睡着了会不会有监测不到的时候呢。”大叔不疾不徐道:“我对自己的身体还是比较了解的,之前在其他医院也做了心脏介入检查,一般呢到凌晨两三点会醒来一会儿,我这时也会自测一下心率,之前背过动态心电图,我知道自己睡眠情况下心率会很慢,但一直以来也并没有感觉到特殊的不适。”
我这时察觉到了大叔或许对我们医护人员的信任并不完全,并且对自身状况也相对的较为自信和固执。在交流中,大叔开始向我聊起了一些关于他的旧事,“我祖辈父辈都是军人,从小的家庭教育很严苛,对男娃儿也是教育‘自强不息,志在四方’,自己十四岁就入伍了,在部队上学习生活训练,日复一日的坚持,在学历的获取后还继续努力专攻,取得了高级工程师证书,在部队上做通讯信息技术工作。这一路有一起成长并肩作战的师兄弟,后来自己也带了很多新兵……年轻时候有过很多负伤,最严重的一次左手负伤,那几年相对于堪忧的医疗条件,医生建议进行截肢,那时的我还正值年轻,接受不了残缺的自己,也无法想象失去手臂今后的人生,哪怕危及生命,也要保全身体,也要保全自我的尊严,时至今日我想我依旧会做出同样坚定的选择。那之后我坚持治疗,坚持锻炼,尽全力去康复手臂的功能,现在使用起来也没有较大的问题了。”
伴随着患者大叔的话语,一幅幅峥嵘岁月的画面在我脑中徐徐展开。至此,我作为护理人员与患者大叔的距离似乎近了一些,但鉴于大叔长期要强的性格和植根自我的确信,目前好似并没有取得足够的信任去说服进行治疗,我还是心怀沮丧的。但同时我仍然坚定态度的建议大叔,希望他积极的配合我们的治疗。这一夜,我都在密切地巡视观察着大叔的生命体征等情况。
第一次的“交锋”我似乎并没有完全有效的说服大叔,但在我心里对于患者的心理疏导比起强迫其进行治疗,我更愿意多花费一些时间和耐心去聆听了解,从而通过循序的沟通去改变患者对于医护,对于疾病的观念。很多时候,作为护理工作者,我们需要去做的比我们能够想到的更多,我也是在一个自我摸索的成长过程中步步前行。

(少年周叔)
亦患亦友
两天后,我来接班,首先就关注了周叔的治疗进展,了解到周叔最终在医护人员和主任的多次沟通后接受了“双腔永久起搏器置入”的手术,并且术后愿意配合使用心电监护和相关治疗,目前处于术后恢复期。我再次来到周叔床旁,这次相对轻松的互相问好后,我也关心询问起了周叔:“您目前术后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感到一些好转?是否还有哪些不适应和不舒服的?”
周叔由于术后还是比较虚弱,心脏起搏器术后也有强制平卧位的要求,限制了活动后只能卧床休息,但看起来心情不错,他闻言道:“小李,我最后还是决定进行了手术,说实话一开始心里面还是会害怕忐忑的,但现在手术很成功,我也在配合着进行术后的治疗。”
看到配合治疗的周叔,我心里是很高兴的,作为护理人员工作有序推进的高兴,也作为我自己看到周叔治疗顺利日渐康复的高兴。可是基于我对周叔倔强要强性格的了解,也预设之后护理治疗能顺利推进,我还是决定和周叔深入的再聊一些,评估一下此时周叔的心理状态。于是我发问:“周叔,您最终是怎么下决定同意了手术和治疗的?”周叔笑笑说道:“你们医护人员很是关心,孙主任也来找我谈过话,我逐渐开始对医护有了一些不太一样的了解,心里也很感谢,同时我远洋在外的儿子也来电希望我积极的面对疾病和治疗,老战友们在得知了我的病情后都在战友群里关心和鼓励我,我想积极的面对治疗才是明智的、有勇气的决定,所以现在我也很坦然的接受,要好好坚持治愈自己的疾病。”
我深感这多方的关心和努力还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但环顾四周,发现周叔并没有家属照顾,由于疫情防控,战友们也没能来探视,只有护工阿姨在照顾卧床的周叔一切起居饮食。我这才和周叔说道:“手术完成只是第一步,后续还有一整套的治疗,心血管疾病需要一个和缓的过程来进行逐步的康复,您要坚持住,好好配合治疗,如果感觉恢复期间枯燥的时候我可以来陪您聊聊天。”周叔欣然应允。后几日的工作中我一有空闲时间便会来和周叔聊天打趣,上下班也会来和周叔问候道别,关系也逐渐发展到了亦患亦友。
周叔住院期间的这十天,从周叔那我听说了他前半生辗转多国起起伏伏的壮志人生,也在周叔的相册留念中领略到了美国华尔街的繁华熙攘,圣玛利亚大教堂的金碧辉煌,越南河内绵延的农耕稻田,热带特色下的人文景观……有时也会聊起关于对儿子成长过程的追溯,对远洋及已故家人的寄思……时时还会提及那些周叔风华正茂的韶华岁月,那些曾并肩的山河故人……久而久之,我也会分享一些关于自己的点滴和迷思,周叔也总会循循善诱,这时候我感觉自己从一个照顾患者的护理人员忽而转变成了一个听取长辈劝谏安慰的小晚辈。
十天之后,周叔接到可以出院的医嘱,可以看得出周叔很开心,但再回头一看,阳光洒进病房,在这个一生坚毅的大叔脸上映射出了一丝柔软和慈蔼。这个依然精神奕奕的大叔和住院初来时的平和而又疏离还是有些不太一样了。就这样,像每一个普通的工作日那样,我们在这天辞别了周叔,祝贺他顺利出院。

(始终在路上)

(出院留念)
写在最后
我还是一如既往埋头在日往月来的护理工作中,但这一路走来遇到的一个个“周叔”让我感觉到了这日复一日里的缝隙,光透射进一间间病房,有细小的微尘在中间起舞。我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做着一份平凡的工作来糊口,少年人做的梦,有时被琐碎和落差打断,后来发现人与人之间感情链接创造的价值或许就是用沟通来实现治愈。护理工作除去专业技术后,剩下的就是纯粹的“感受”,那些有温度的护理就像时间的推移,日复一日的疗愈,润物细无声,灌溉从始至终。
周叔的住院故事写完了,但我想周叔之后的生活还在别处继续,而我作为一名新人护士,我这一生的护理故事将会漫长的续写下去。想起当初作为护生懵懂的自己,许下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生誓言,今时今日作为一名护士的自己才发现看过了更多世事后的任重而道远。
我想医院不仅仅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地方,也是一个向死而生的地方,而护患的沟通是一场场双向的治愈和成长。再强大坚毅的灵魂也会有病痛侵袭和难忍的脆弱,再神圣的职业也是一个个凡胎肉体在日夜更迭中转动着齿轮,可是再渺小的一个个平凡的存在也都努力向死而生的在人世间行走着,病痛会得到治愈。我们每一代护理人也会在披星戴月的职业生涯中找到那束自己的光。那些和我一样身在一线一路而来,时感迷茫但必须坚毅的护理同仁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望共勉。
花絮
完稿当天,收到周叔送来的感谢信。他也没忘记我们,心心念念的回来看看。细读这封信,字里行间显真情,也是和谐医患关系的最好诠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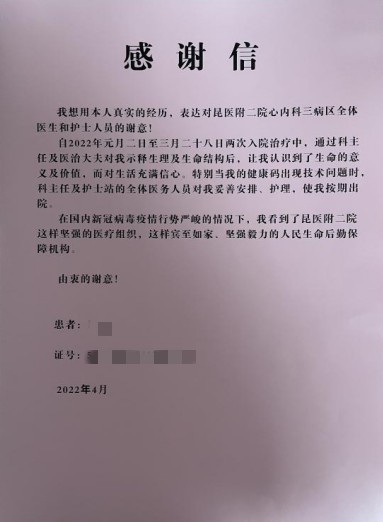
(文中人物故事及图片来源均征得当事人同意)
文图:心血管内科三病区 李明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