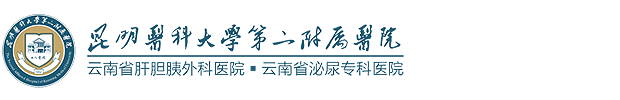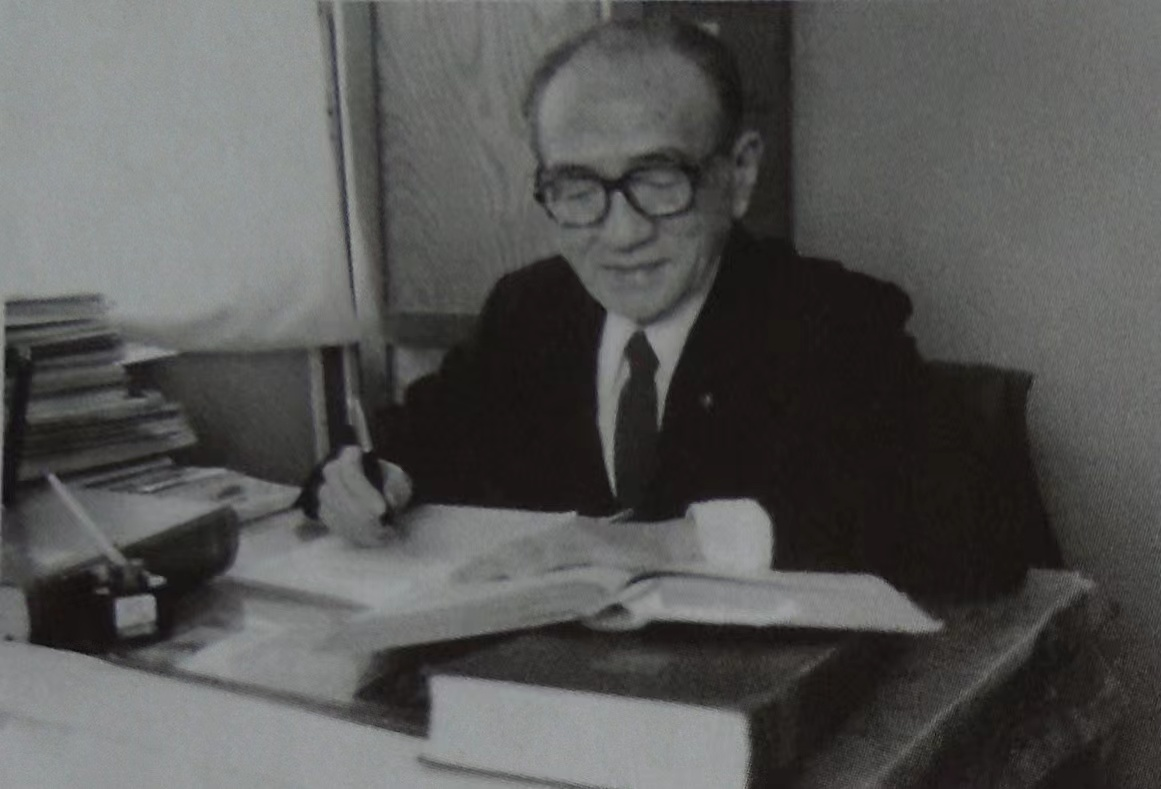
胡同增教授,男,天津市人,1924年出生。1949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医疗系,同年到昆明市护国医院任住院医师,1951年到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现在的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任外科助教,1952年参加谢荣教授在昆明主办的为期3个月共11人参加的麻醉训练班,结业后从事临床麻醉工作。退休前胡同增教授为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麻醉学教研室教授、麻醉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国外医学麻醉学与复苏分册》编委、云南省外国语学会名誉理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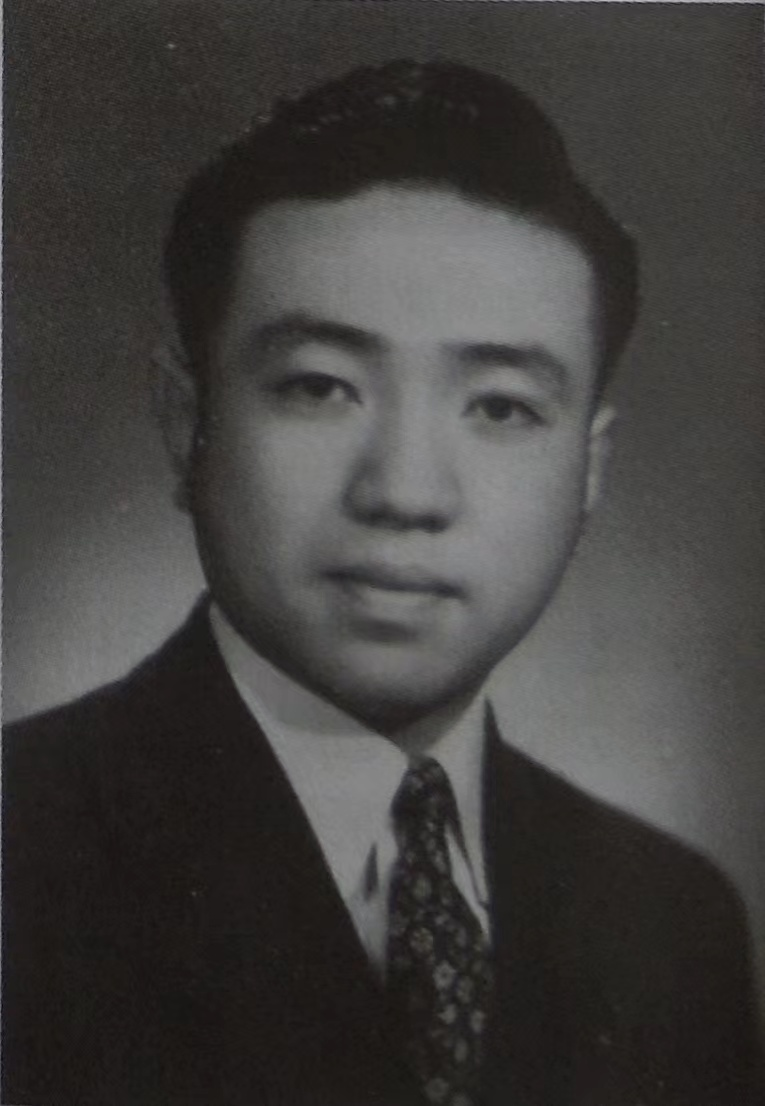
年轻时代的胡同增教授
胡同增教授是云南省第一位专职麻醉科医生,他十分重视麻醉学的临床实践和实验研究工作。1952年,在谢荣教授3个月的麻醉训练班里,他们晚上上课,白天做麻醉,系统地学习了麻醉学,包括术前准备、麻醉监测(含乙醚麻醉分期)、术后随访,同时也系统地进行了现代麻醉学的规范学习。
在学习吸入麻醉时,除学习乙醚麻醉外,还学习三氯乙烯麻醉、气管内插管技术及上海陶根记牌麻醉机的原理与临床使用,还学习了普鲁卡因静脉全身麻醉(由于当时云南没有该药物,因而未能示范)。培训班结束后,11位学员均回到各自的医院,回到各自原来的外科学或妇产科领域,唯独胡同增医师留下来专门从事临床麻醉与相关教学工作。他认真按照谢荣教授的教导,在医院建立从术前访视到术后随访的制度,提供完整和规范的麻醉记录。在完成大量临床麻醉工作的同时,还认真落实麻醉工作制度与规范,积极开展腰麻(以后才分出了鞍状、单侧腰麻)、乙醚全身麻醉,并实行气管内麻醉。此外,胡同增医师还积极探索和开展了静脉普鲁卡因麻醉,他通过朋友想方设法与当时的昆明制药厂联系,申请特殊分装5g/瓶的普鲁卡因粉剂,以利于开展普鲁卡因静脉麻醉时使用。他专注鼻咽癌切除术中静脉普鲁卡因麻醉的应用,并积累了很多经验。他积极撰写静脉普鲁卡因麻醉相关论文并发表在1954年的《中华外科学》杂志上。最初是10例报道普鲁卡因静脉麻醉的介绍,之后至1957年间又相继发表了静脉普鲁卡因与唛啶复合麻醉等3篇论文,是我国较早对普鲁卡因静脉麻醉的报道。
1958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期,胡同增教授一直被下放农场,复职后他回到昆明。从1980年开始,他与动物实验室同事合作,进行“硫喷妥钠、γ-OH复合动物麻醉”的研究,总结实践结果,发表于昆明医学院学报(1984),1986年他主编的《实验外科学》专著,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另有《东莨菪碱对动物失血性休克的实验观察》及《安氟醚麻醉》等与同事合作文章,在全国性学术会议上交流。上世纪80年代他撰写《实验外科基础知识》(讲座),连载刊登于中华实验外科杂志(自1986年第4期开始);在译作方面,除有多篇综述及译文刊登于《国外医学》麻醉学与复苏分册和《昆明医学院学报》译文增刊外,尚有与另一位同道共同编译的《临床听力测验》一书,也于1987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此外参加《耳显微镜外科手术学》的编译工作,担任其中有关麻醉学章节的编写。他曾受委托完成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标准工具书《卫生词语汇编》中译本的审校工作。胡同增教授多年来在编著译作方面孜孜不倦,共有专著书籍、论文、综述、译作等80余篇,他工作勤奋,数年间成稿逾50万字,为促进学术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上世纪90年代在昆明医学院附二院主持研究生答辩。由左到右:胡同增教授、蓝瑚教授、李彦教授、杨文儒教授、文士铭教授
胡同增教授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在从事临床麻醉工作的同时,即开始麻醉学教学工作,1954年编有油印版《临床麻醉手册》,之后又编写专修科麻醉学讲义等教材和《实习指导》等,在医学院内部印发供本科及专科医学生学习。他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积极研究国内外先进的教学思想,不断改进课堂讲授,曾推行“发现法”讲课,注重在教学活动中不仅传授真理,更注重教会人们发现真理,即更关注“授人以渔”,他的努力与实践收到了良好效果。他著有多篇教学法论文,如《临床麻醉学课堂讲授工作中的几点体会》和《医学院附属医院中教学和医疗工作统一的问题》等。
2009年一月的一天,当笔者作为新一届云南省医学会麻醉学分会主任委员来到胡老家中拜访时,85岁的胡老满怀欣喜,他精神矍铄、步伐矫健,侃侃而谈。谈起上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麻醉学科初创时的情景,他对当时简陋的条件与物质、药品的匮乏万分感慨,同时更感慨那时的工作热情与全力以赴;谈起之后20余年下放农场的岁月,回忆在边远的山村、在土房雨伞遮灰的条件下,他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与技能为当地患者服务,多次进行紧急手术,成功救治患者,以及在当地培养中初级医务人员场景时,眼含热泪,真情流露,让人深深感受到他战胜困难的坚韧与对事业追求的执着;谈起学术,胡老依然思路清晰,睿智而严谨;谈到人生,胡老平实而宽厚,有许多充满哲理的感悟。临别前,除了对后辈的热情鼓励之外,胡老还赠送了他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那本油印版的《临床麻醉手册》。
胡同增教授于2021年因病去世,享年97岁,他对生活的积极与热情,对苦难的乐观与豁达,使他的一生始终保持着一颗慈善而求实的心。他是医者生涯的一座灯塔。
来源:2012年《人物与历史》杂志 衡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