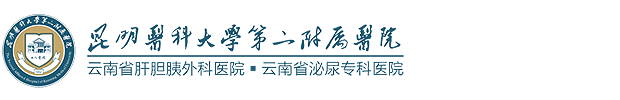丁佑青,1930年出生,成长在一个特殊而充满挑战的年代,漫漫学医路,使她仿佛拥有了一身铠甲,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在这个浩瀚的世界,发出自己的光亮,照亮了别人,也照亮她前行。
医护兵 基层医生 篮球队员 她很“全能”
丁佑青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小学还未毕业,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她从昭通彝良县城到昭通市继续读书。从昭通女子中学毕业后,考取了昆华高职医院学校,从此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家中兄弟姐妹较多,父母也已年迈,在高职就读期间,她半工半读完成了学业。在校期间,对于学习她丝毫不敢怠慢,因为她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份责任,只有使自己变得强大,才足以配的上这份光荣的职业。
从昆华高职医院学校毕业后,丁佑青加入了革命地下外围组织——滇中独立团,成为一名游击队员。“我自知我的力量很微小,但仍想竭尽全力,为这个我所热爱的国家奉献自我。”1949年,丁佑青跟着大部队到玉溪远足,为避免暴露目标,她们通常在夜里行军。行军路上充满了各种不确定,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作为当时队里四名医护兵中的一员,丁佑青一行人承担起了整个队的医疗健康服务。怕暴露身份,就想到了起绰号。因为她是小队里面跑得最快的,从此“轱辘”成了她的代号,现在回想起来,不免觉得有些趣味。如今提起当年的情形,丁老仍激动不已。在她们营救一名受伤的机枪手时,丁佑青眼疾手快,使出了全身力气,独自把他拽回了安全区,之后连她自己也惊呆了,想不到自己还有那么大的力气。在行军途中,除了救死扶伤外,他们也要向当地的医务人员传授医疗技术,一顿饭就已经是最好的报酬,如果当地医疗能因为他们有所发展,那便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在那个医疗水平落后的年代,缺医少药,条件非常艰苦,遇外伤病人时他们就就地取材,把抹布洗干净消毒后当绷带使用。在扬武镇时,当地人民患上了一种疾病,俗称“打摆子”,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疟疾,但是当时的人哪里知道这些,只知道得了这种病会要命,对于得病的人就远离他们。在人人自危的时候,丁佑青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进入“病魔”营地,不顾危险,从病魔手里抢人。他们争分夺秒,轮流换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那时他们最怕的事情不是自己生病,而是生病后就不能继续参与工作,相比劳累,他们更怕自己不能医治患者。终于,在他们细心照料下,当地老百姓逐渐好转,疫情得到了控制。
在校期间,丁佑青同样热爱运动,积极参加各种篮球比赛,入选了云南军区体育工作队,她们的球队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云南省燎原队,她还被评为了“先进女子篮球队员”,在与省队进行较量的时候打赢了省队,现在谈起仍感到自豪。在解散女队后,丁老的工作调整到了云南省卫生厅。从此,她开始在昆明市工作。通过在党校的学习,她去到了五二四医院人事科,直到后来开始组建工人医院。
对工作竭尽全力 对孩子却心怀愧疚
据丁佑青老师回忆,组建工人医院时,他们还要自筹资金,一边是工作的繁忙,一边是筹集资金建医院的焦虑。医院门诊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但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水,打乱了他们原本的计划。“医院的基础办公用品都被大水淹了,没有办法,越是困难越应该向前。”于是,第二次筹备组建医院的工作开始了。这次工人医院扩大了建设规模,在之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成长为了现在的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工人医院刚建立时,来看病的大多是生产队里年纪比较大的大爹和大妈,他们为各自的生产队努力工作,同时也落下了一身病根。丁佑青老师见这些人不容易,和医院领导商量把他们留下,让他们在医院里打零工,养活自己和背后的家庭。
在几十年的从医生涯中,丁佑青活到老学到老。据她回忆,有一个气管异物的患者来看病,由于她们不太清楚气管的解剖,还亲自跑去向李秉权和胡素秋教授请教。
医生的工作平凡而伟大,琐碎而不易,艰辛而又劳苦,她们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一份份充满信任的重担。在医院,她们是医生,在家里,
他们是子女、父母。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为患者服务就代表要舍弃部分陪伴家人的时光。对于孩子,她充满了愧疚。在孩子只有两岁的时候,因为工作将孩子独自锁在了家中,不知哪里来的火苗,点燃了房间,好在最后孩子没大碍。或许有些事情是可以耳濡目染的,她的两个儿子,一个选择成为保卫国家的人民子弟兵,另一个选择在医学院工作,继续从事医学教育工作,培养出更多与母亲一般优秀的人。
听完丁佑青老师的故事,我想起了入学时的起誓,“我谨以我的生命起誓:为了全人类的健康,我将奉献出我的毕生精力......”确实,丁老师奉献出了毕生精力,只为对得起医生这个称呼。对年轻的我们,丁老师也送出了寄语,希望我们能肩负起医生这份职业,沿着她们的脚步,放开手、大胆干,走得更远更长。
文:离退休管理办公室 团委李佳芬、吴丽秋、毛梦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