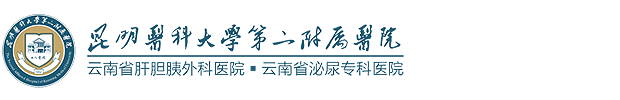1962年7月经云南省政府决定将昆明市工人医院改为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1963年10月在蓝瑚主任、罗应昌主任带领下,由昆医附一院调“外总”、“内基”两个教研室共32人到附二院和原工人医院留下的部分医护职工一起,全面开展了医院的内、外科的门诊、住院部和教学工作。
附二院建院时的年轻医生们, 61级的张炳彦、徐鸿毅、白中华、张云华、杨曾铭、陈霭菊、马月婵、张然、王福,62级的黄安邦、李质彬、郭江城、张乾玉等。此时,从昆医63级毕业的王炳煌、郝复、陈兰娇、徐章、袁玉仙、吴荣芙、陈孔仪、赵定真分配到附二院工作。第二年64级毕业的彭荣宗、杨尔麟、郝锡昌、周明非也分到附二院,另外还有护理部的冯毓娟、沈丽英、李景云、万俊、许秀英等。这一伙年轻人明白,要在一个条件较差的普通临床医院的基础上建成一所集教学、医疗、科研为一体的现代教学医院是不容易的,需要大家不断地努力奋斗,刻苦钻研业务技术,要用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年轻人们下定决心要在主任及各位老师的带领下,努力学习,练好本领,从零做起,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来。

附二院建院时的内科医生1964年摄于附二院住院部前,(由左到右)前排:张然、郭江城、徐章、郑凤兰、明其坤、谭正肃、颜可贞。后排:郑信坚、杨尔麟、太品荣、白中华、杨曾铭、陈宗荫、明庆华、进修医、马月婵、进修医、陈蔼吉、肖泽方、陈兰娇、进修医、罗应昌。
“三基”训练为他们打下坚实基础
当时,医院党政领导及教研室非常重视对这一批年轻人的教育培养,给每个年轻医生指定了指导教师,制定了严格的师资培养计划。年轻医生们按照教研室的要求制定出各自的学习计划。对年轻医生的培养,重点要加强他们的“三基”训练,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
理论学习是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系统地阅读教材、经典著作及相关的医学杂志,并要求写出读书笔记和杂志阅读卡片,每月一次交给指导老师检查、修改。对初参加工作的医生每半年要进行一次考试,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对年轻医生的临床工作要求也十分严格。当时,每个住院医生分管4~5张病床,要求对所管的病人要写一年的全病历,每份病历大约要写12、13页。要详细记录病程日志,把病人的病情变化、治疗反应、医生的分析意见等都实事求是地记录在日志上,在没有电脑的时代,这样的书写工作量还是很大的。

徐章和他的指导老师肖泽方主任(1964年摄)

附二院住院部楼前的徐章医生(1965年摄)
年轻医师进入病房后,上级医生就对年轻医生们说:“住院医生是在病人的床旁长大的”,要求住院医生要多进病房,多了解病情,多接触病人。住院医生每天早上7:30进入病房,了解病人一夜的病情有没有什么变化,并熟记所管病人的病史、体征及各种检验数据,待上级医生查病房时全部背诵汇报,上级医生则随时当众纠正错误,一旦错误过多自己会很难为情。下午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进病房看病人,问问病情,解答病人提出的一些问题,还要做一些如:胸穿、腹穿、腰穿、骨穿、肝穿等技术操作。无论上午还是下午离开病房前,也都要到病房看一下病人,问一问病情变化,交代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在交班报告上写好危重病人的注意事项后方可下班。医生和病人接触的多了,互相得以沟通,病人的问题能得到及时解决,就能很好地配合治疗,医患关系十分融洽。
教研室十分重视年轻医生基本技能的训练,为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要求参加工作第一年的住院医生所管病人的三大常规(血、尿、大便常规化验)必须自己完成,不得送到医院化验室做。当时内科自己有一个小化验室,有三台显微镜及一些做常规化验用的试剂、试管,没有任何电子测试仪器,住院医们取了血液标本后,在这间化验室里用最基础的血细胞计数池在显微镜下认真地计数血液细胞。当时是大内科,什么系统的疾病都要管。他们除了做三大常规外,遇到消化道溃疡病时,还要做大便潜血、胃液分析、胃酸滴定。还要为血液病人做骨髓细胞检查。在血液细胞分析中,最难的就数骨髓细胞分析了。陈宗荫医生是搞血液病的,大家就请她指导看骨髓片。在上级医生的指导下,年轻医生给病人做骨髓穿刺,自己推片,自己染色,在陈宗荫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骨髓细胞分析。大家的学习劲头特别足,一个人发现有什么典型的、特殊的骨髓细胞,全科的年轻医生都争着来看,不放弃任何学习机会。有时候三台显微镜同时看骨髓,大家都争着请陈医生指导,这个叫“陈医生来帮看看这个是什么细胞?”那个又喊“陈导师请帮看看这个是不是原始红细胞?”陈医生被忙得不亦乐乎,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年轻医生们对骨髓细胞的识别都有了明显的提高,陈宗荫医生也得到了一个“陈导师”的美名,一直叫了一辈子。

徐章医生在内科化验室(1965年摄)
当时医院没有担架队,也没有推车,科室放着一副担架,一些不能行走的病人开了照片单后,则由年轻医生用担架抬他们去放射科照X光片。病人去世了都是由年轻医生和护士做遗体料理,帮遗体擦身,穿衣服,包裹尸体,然后抬到停尸房。护士很怕夜间病人死亡,料理好尸体后,多是由年轻的男医生抬前面重头,两个护士抬后面,经过一段路灯幽暗的菜地,到达停尸房后,要把停尸台上的铁罩子一个个掀起来看,空的才能放,要是里面已经停着一位,常令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建院初期交通不便,各单位也没有汽车送病人来院急诊,门诊虽然不多,但要负责黄土坡、马街工厂特约单位及西山区团结乡农村的急诊,夜间一旦总机接到电话,直接通知门诊医生叫上李立仁师傅开着医院唯一的一辆老雪佛兰救护车到工厂、农村抢救病人或把病人接到医院治疗。这样,大大增强了附二院与周边工厂、农村的关系,对年轻医生独立工作、急诊处理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提高。
通过在临床实践中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年轻医生们的业务能力提高特别快,为他们今后的临床发展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他们的地方都生机勃勃
这一批年轻人不但努力学习业务技术,还积极要求进步,建院初期各种事务性的工作比较多,无论是义务劳动、清洁卫生等,他们都积极参加,专捡重活、累活干,处处表现得朝气勃勃、生龙活虎。
那时候每个星期有一次义务劳动,除了搞好病房卫生及各科室划分的环境卫生区域外,还要完成医院安排的各种劳动。年轻人们都积极投入,带头劳动,擦玻璃、拖地板、除杂草、通阴沟,不怕苦、不怕累,积极完成各种劳动任务,尽量把医院搞得更卫生、更漂亮。遇到秋收季节,还会组织我们去帮助邻居麻园村的农民秋收,麻园村有八个生产队,所以大家都戏称我们是麻园九队的。
1964年新建烧伤病房、手术室(现3号楼),为了病房早日建成,组织青年们每天晚饭后义务劳动,把运到工地上的砖头搬到脚手架上,便于工人第二天上班即可投入工作。那时年轻人们都住在医院宿舍,吃完晚饭大家自觉地来到工地排成一行传递砖头,由于人比较少,战线越拉越长,速度越传越快,不但在平地上传,还要将砖头抛上二楼、三楼的脚手架上,一不小心,黄安邦一块砖头飞到了徐章的鼻梁上,顿时鲜血直流,赶快到门诊缝两针包起来,回来接着又干。
进入医院的路边有一块砖砌的黑板,是由共青团附二院总支负责的宣传栏,也是附二院对外宣传的唯一阵地。这块黑板报刊名叫《春潮》,每月出一期,简要地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医院好人好事、医学科普、卫生常识、诗歌、散文及医院通告,路过的人都要注目观看。从撰稿、抄写、绘画、出版均由徐章、郭江城负责,起到了一定的宣传教育作用。
当年附二院有一支不错的篮球队,由张炳彦、王福、陈孔仪、范义春、徐章、李立仁、吴光灿、丁子文等组成,当时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如今已是八十四、五的老人了。本着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宗旨,分别邀请周边工厂进行篮球比赛,从西站的汽车总站、开关厂到黑林铺的电池厂、汽车技工学校,几乎都与我们比过篮球,我们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当时打球不讲究条件,不要补助,甚至连统一的队服都没有,各人穿各自的衣服及胶鞋就去打球。1965年昆明医学院开职工运动会,有附一院、附二院、医学院及所属十多个单位参加,附二院男篮获得篮球比赛冠军。颜义泉院长观看了篮球决赛对我们说:“你们的篮球倒是打得好了,就是衣服太差,像个杂牌军,给你们发点球衣吧。”我们说:“院长,我们不要球衣,给我们买副篮球架吧。”后来医学院真就奖了一付标准铁质篮球架给我们,至今还在附二院篮球场上。

附二院篮球队队员
成长为各学科业务带头人
附二院建院初期的这一批年轻人,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医学院、医院各级党政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教研室各位老师的认真培养教育下,他们严格要求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医德好、医风正,刻苦努力、永跟党走,在医疗及教学实践中,刻苦钻研,提高业务技术,很多人成了医学专家或各个学科的业务带头人。
当年的这批年轻人现在也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而如今的附二院高楼林立,设备先进,技术精良,人才齐聚,已是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为一体的现代教学医院,是云南省
著名的三甲医院。它的今天,浸透着六、七十年来几代附二院人的汗水和努力,也期待着新一代医者能够继承传统,续写辉煌!
(本文感谢白中华主任指导)
文图:徐章